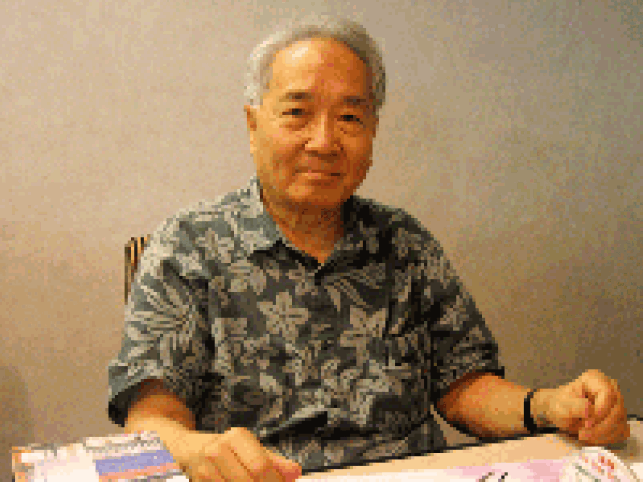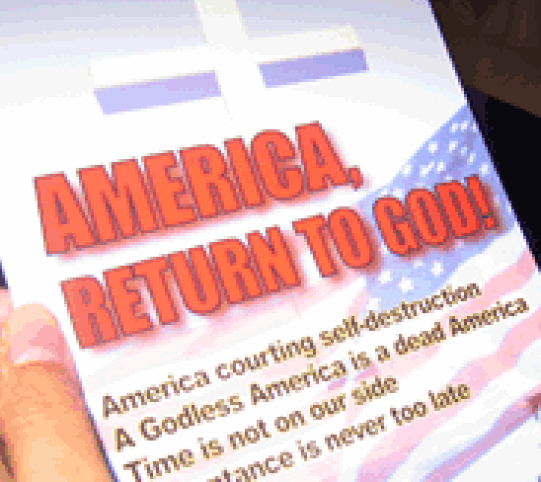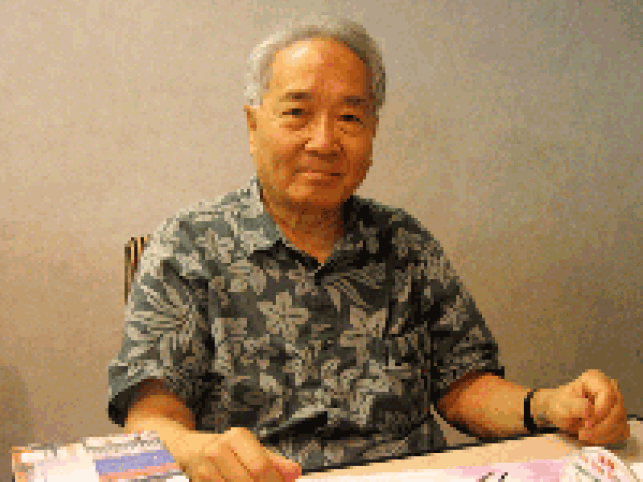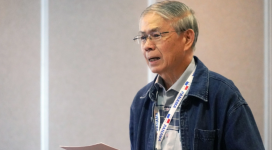为了参加"普世教会事工推进会"创办人张子华牧师的纪念活动,"大使命中心"会长王永信牧师近日专程到访香港。在上周日他的80大寿的庆祝聚会里,王牧师分享了他的未来事奉的方向。虽已届晚年,他仍尽用心力于福音和宣教事工上,事奉神的热情丝毫未有减退。
今天本报有幸邀得王牧师在紧迫的日程挤出一点时间,与本报做了一次专访。他一生的事工、现今教会的问题、美国的问题、以及香港的信仰情况,都一一与本报分享。
王牧师,您先后创办了不同的事工-—中信、洛桑、华福、大使命中心,和近年的"基督徒关怀社会基金会"、"支持一男一女婚姻协会"等。在上次你80大寿聚会上,您见证说自己的事工的方向上并没有事先计划。那么,现在你回头看,你觉得这些不同时期开展的事工之间有著什么关系?
是的,我自己没有预先的计划。我每走一步,神就给我开一扇门:神知道我的需要是什么。他先训练我,然后给我下一步;祂再训练我,又再给我下一步。.如果没有中信,不可能有洛桑;如果没有中信的经验,我不能作洛桑。中信是在美国教会开始,华福是向著世界的华人教会。所以,没有中信的经验,就没有华福。同样地,没有洛桑,也不会有华福。没有华福,就不会有"主后二千福音运动"(AD2000 & Beyond Movement)。
虽然是神开路,但是祂有祂的计划,一步一步的训练我。God knows what He is doing。
回想这几十年,您觉得最难推动的是哪一个事工呢? 困难在哪?
其实,都困难,但有最困难的,就是打破传统——华人很多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在华人中,推动大家合作很不容易。
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华人爱家庭的传统是全世界有名的。师母(王永牧师的太太)以前在香港生活的时候,她去九龙城的市场买菜,她跟卖菜的老人家谈话,得知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在美国,一个在英国。他们为了供养他们的女儿辛苦地工作。这是中国人的美德和传统:家里的父母吃苦,支撑和凝聚著一个家。
但这同时有副作用,就是形成我们内向的文化。我们从小都是"家"的文化:各家自扫门前雪,但家以外的就不多管。
但我们成了基督徒,也把这种传统不知不觉也带到教会来。信徒只每个星期去教会,教会以外和宗派以外的教会则没有来往。因此华人教会一体和合一的情况很差。
第二就是教导。教会的教导中,对"教会"这两个字的意思是理解不全面。
"教会"指的是面前看得见,摸得到的本地教会,但教会还有第二个意思的。但我发现教会没有讲这个,牧师讲道时也没有教。教会的意思还指"普世的教会",但这教会指的是"相信圣经的教会",现在有不相信圣经的教会,那些就不用谈了。
很多教会只教导了第一个意思。牧师都说要爱教会、服侍教会,如此大家想到的只有自己的堂会,却少谈我们的整个身体-—the universal body of Christ——这是主整个的身体。这一层意思教会很少讲,所以弟兄姊妹整天都在自己的教会里,对于整个身体的关心很少,这是第二个原因,造成了今天教会欠缺神的国度的观念和心胸不够广阔。
那么,教会可以怎样突破这种状况呢?
要突破的话,牧者先要有突破;牧者要有突破,神学院先要有突破。神学院的领袖老师开始要先有广大的心和国度观念-—the Kingdom Concept——这是华人教会很缺乏的。
提到神学院,台湾有基督教媒体批评现时的神学院未能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人,学生欠缺媒体和资讯方面的专业知识。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您认为今天的神学院具体应该进行哪方面的改革呢?
神学院和教会都说要有partnership,强调知识和灵性并重。但事实上,神学院都走知识、学问和学位的道路。基督教不是反知识的。一个事奉主的人必需在知识和属灵生命上有一个平衡。
至于改革,其实就是整个神学院和教会世界观的改革,有了这个作为一个基础,再谈该怎么作;就是说,先要看见我们今天所要作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要作的是什么时,才有真正的方向和目标。这样才能知道我们教会要找什么样的传道人。他们知道了以后,神学院才知道要供应怎样的传道人。
你明年二月将会出版一本书,书名叫"America Return to God",这本书是针对美国哪方面的问题呢?
从16世纪开始,人文主义兴起。简单来说人文主义就是擡高人、讲自我,把神的地位降低,所以这主义叫humanisum——the emphasis is on man。所以从16世纪起,人是万物的尺度,人的自我提高。在19世纪未,自由主义新派的学者起来,他们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不相信耶稣是圣灵生的儿子,不相信基督的神性,慢慢就演变成一个情况:人不需要神。
美国是神建立的,美国开国的元老都是基督徒。美国钞票上都印有"In God, We Trust"—-我们相信上帝。但最近50年,他们离神越来越远了。美国的公立学校现在不容许祷告、读经和讲福音,法院内不准挂十字架和诫命,他们说不要宗教了,更不要基督教了,所以美国离神越来越远。
西欧离开神,美国则跟著西方走。加拿大亦然。我们看著这样的危机,我们要出一本书。我们盼望这书明年二月能出来,把它寄给美国各阶层的领袖。我们希望,我们作为今天约拿的角色,引领人们悔改。
这次您来香港,您觉得香港的教会气氛怎么样?
第一,香港的思想和错觉走在前面,对于美国和加拿大的华人,这些则在后面。就是说,香港人对于自身的观察很敏锐;第二,这里滙聚华人教会的精英,所谓精英就是人才。
前面讲的都是好处。后面讲的就是不好的地方。
第三,这里有自守的情况,外展很缺乏。可能受了环境的影响吧。有中国—-"老大哥"在旁边,在他们心里某程度上受到了影响;不要因为大小环境的情况变成内向,要往神的国度展开。
第四,我觉得香港的教会在圣经的根基上要站得住。拿同性恋问题为例,教会的观点就跟圣经不一样了。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同性恋是罪,但他们不断的绕圈子,说:"圣经虽然这样说,但是什么什么……",他们有"但是"。
教会跟著世界走。有一句话说得很对-—教会怕得罪人,但是不怕得罪神;教会宁可得罪神,不怕得罪人。他们跟著大众走,大众的意思怎样,领袖就跟著走,没有道德原则和信仰原则,随著群众走。为要得著支持和选票。这是教会可悲的现象,这是民主国家的可悲现象。
所以我常说:"民主和独裁都是人本主义"。人家常问我为什么这样说。民主和独裁,两边都是人本主义,分别只在于独裁是一个人,民主是一群人,但说来说去都是人本主义。
民主制度是人所能发明的政治体系中最好的。Best political system conceived by man. 但是,民主有它的极限,the limitation of democracy。为什么?"多数统治",这个思意的根基是:一个、两个可能会错,但多数不会有错。这个体制在一个好的基督教背景下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当大多数的人都败坏了,那怎么办?这个民主还有什么盼望?就像现在比利时、荷兰、丹麦、西班牙和北欧等国都是同性结婚合法的国家。看看加拿大,美国也跟著他们走。我们要注意到这些全都是经过多数人通投票过的法例,都是通过了民主的手续而生的。
所以,不能用民主的方法解决问题,因为民主还是人本主义,所以说到底,还是要回归神。人是可败坏、可沉沦的——不管是一个、还是一群。所以我们要回到上帝面前。
后记
眼前的王永信牧师说话十分有"中气",一点也不像年届80的人。王牧师多年来靠著绝对的信心开始了不少具历史性的华人事工,他的信心影响了整个华人基督教界。看到他的白发,只能想到箴言里的一句话:"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