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球逾12亿天主教徒的精神领袖,已故教宗方济各以其简朴亲民的形像赢得"人民的教宗"美誉。然而,在堕胎、变性、难民与伦理等社会议题上,他一再采取"包容"路线,引发部分保守派批评,甚至认为这种立场动摇了教会的神学根基与全球影响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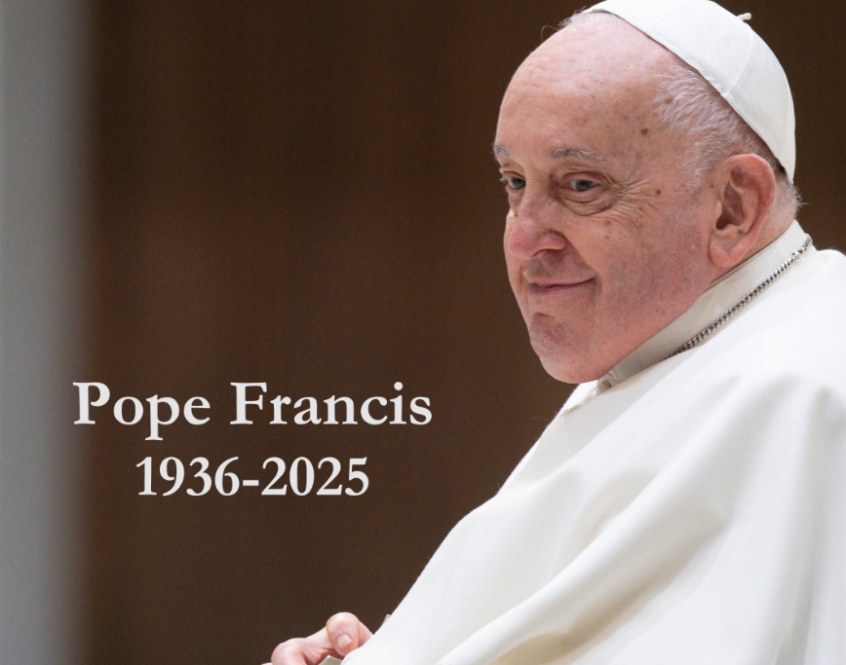
近日,旅美华人牧者陈佐人在《询经问道》节目中发表评论,直指已故教宗方济各在诸多争议中"明哲保身"。作为美国西雅图大学神学系教授,陈牧师拥有深厚的神学背景,曾师从天主教思想家特雷西(David Tracy),并长期在天主教大学执教。他以特有的幽默和洞察力,讲述方济各的生平,甚至调侃美国天主教的信仰困境,称他们"难以找到信仰的家园。"
在陈佐人看来,教宗方济各的人生轨迹与神学立场显得颇具争议。方济各本人曾坦言自己并非神学家。陈佐人笑称,方济各"神学根基薄弱",他16岁才成为修士,相较于许多自幼进入修道院的人,他的早年生活更为"世俗"——他热爱足球、舞蹈,思想活跃。由于学科背景为数理化工,早年主要教授数学,自然难以建立起系统的神学架构。
在阿根廷服事期间,方济各曾因持保守立场而受到同僚排挤,被迫调往偏远乡村任教。具体说来,就是方济各曾对抗"解放神学",反对其背后潜藏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与"以救济穷人为假口号"、实则面向将教会掏空的社会行动,因此受到同侪排挤,被迫离开主流。
方济各后来因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提拔而重新回到主教序列,最终晋升为阿根廷大主教,并在2013年成为教宗。陈佐人称方济各是"保禄二世的胜利军",当时若望·保禄二世大力整顿自由派神职人员,尤其在美国任命了许多持守传统立场的主教,形成一批至今仍影响深远的保守力量。
然而,方济各在教宗任内却展现出完全不同的路线。陈佐人批评他在性别、社会、外交等议题上走"彩虹路线",即倾向自由派、多元文化主义。他认为这背离了若望·保禄二世当年所坚持的教义立场。
此外,方济各的过去也饱受争议,尤其是他在阿根廷"肮脏战争"(Dirty War)期间的角色。所谓"肮脏战争"是指在20世纪70至80年代,阿根廷军政府实行的极权统治与镇压行动。当时,在独裁者统治下,许多异议分子、民主运动支持者、甚至普通公民被秘密逮捕、酷刑与处决。方济各的神职生涯正与这一时期重叠,因此外界对他当时的角色有诸多争议。
一些人批评方济各在军政府执政期间未能挺身而出,特别是在有两位神父被捕并遭酷刑致死的事件中,质疑他未尽保护责任。然而,也有不少当时的证人及历史资料指出,方济各在极为危险的情势下,曾通过各种方式掩护并救援多位神职人员,有些甚至因此幸免于难。虽然当时很多人期待他公开对抗政府,但他显然采取了更隐蔽的策略。
陈佐人进一步指出,虽然有关方济各是否涉入"肮脏战争"的争议持续至今,但在他当选教宗之后,有数本重要传记迅速出版,为其"洗白"形像。这些传记引用大量人证,甚至包括昔日批评者,转而称赞他在独裁政权下展现勇气、营救受难神职人员。尽管如此,陈佐人用四个字来概括方济各的人生风格:"明哲保身"。借用李嘉诚的说法,就是"在商言商"。
陈佐人指出,方济各曾在接任本笃十六世之后对媒体表示,自己将效法本笃的榜样,会在身体状况不允许时主动请辞。但事后并未履行这一承诺,依然坚持在任,表现出对权力的眷恋。如今,方济各在任期离世。陈佐人牧师认为方济各"不守信用",并半开玩笑表示,自己曾一度有冲动模仿电影《教父》场景,携带红布前往梵蒂冈,站在教宗床边劝其"辞职",强调"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在陈佐人看来,方济各不仅恋栈权位,还在任内大幅加速任命红衣主教,意图在卸任后确保有继承其路线的"克隆人"当选为下一任教宗。他将此比作拜登总统在任期末加紧提名法官以影响未来司法走向,认为方济各的举动同样是"布局身后事",希望巩固其神学与政治路线不被逆转。
他进一步指出,教廷内部存在明显的路线之争:若望·保禄二世与本笃十六世代表保守主义阵营,而方济各则代表激进派的彻底翻盘。这种"宫廷斗争"已成为梵蒂冈结构的常态,简而言之,就是"保守派与激进派之争"。
陈佐人借此引出一个地缘政治的观察。他指出,梵蒂冈虽然宣称注重全球多元文化,尤其强调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代表性,但从红衣主教的国家分布来看,仍是欧洲中心主义。他建议查看维基百科的红衣主教分布列表即可得出结论:绝大多数红衣主教仍集中于欧洲,甚至单个欧洲城市(如德国的科隆、法国的里昂、意大利的都灵)拥有的红衣主教数量,可能多于整个亚洲或非洲。
他进一步指出,即使选出非欧洲籍的教宗,其文化与种族背景也深具欧洲色彩。例如阿根廷虽位于南美洲,但长期被视为"非南美化"的国家,其人口主要为欧洲移民后裔,缺乏本地土著血统。这也解释了为何二战后许多纳粹战犯选择逃往阿根廷,因为其种族与文化背景更接近欧洲。他以此类比为"上海人不能代表中国人",指出"阿根廷教宗不能代表南美洲"这一看法在拉美本地普遍存在。

陈佐人继续分析指出,理解天主教的结构与教宗的选举,必须从"宫廷政治"的角度来看,不能只用神学或属灵的眼光去理解。他强调,梵蒂冈的"社会道德价值观"是不可动摇的,如同铁轨一般,即使是教宗本人也无权越雷池一步。例如,天主教坚定反对堕胎、同性婚姻、变性行为等,这些被视为"天条",哪怕是方济各也无法公开违反。
虽然方济各在某些议题上显得立场模糊,例如曾对同性恋伴侣表达"祝福",但他从未明确反对同性婚姻,也未推动女神父制度的合法化。陈佐人指出,即使方济各一度有意在其任内突破这些教义底线,他周围的红衣主教"也会镇住他",可见教廷内部的力量制衡非常强大。他形容教宗"有如毛泽东",而其身边的人则如同"周恩来",掌握著实际的战略与操盘权,暗示周边顾问可能比教宗本人更有实质影响力。
进一步谈到教宗的"实权"时,陈佐人认为,虽然方济各在教义上不能随意更动,但在外交领域却大有可为。他类比美国总统指出,教宗在"外交与关税"般的领域具有主导性,其中最关键的议题之一就是"中梵建交"。他说,这关系到是否选出一位"中粉"的教宗。如果教宗亲中,"中梵建交就像搭上日本的子弹列车,会被加速推进";反之,如果继任者如若望·保禄二世那样坚定反共,那这个议题就会被"冷藏在地窖里,永不见天日"。
尽管如此,梵蒂冈的道德立场仍然牢不可破。他强调,这些核心伦理立场是由教宗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以教宗文告的形式定下来的,其中最具标志性的就是《神圣的生命》(Evangelium Vitae)。这篇文告堪比《美国独立宣言》,确立了天主教社会道德的主线。因此,即使是改革倾向明显的方济各,在美国也无法赢得广大天主教徒的认同。
陈佐人指出,美国拥有约6500万天主教徒,但历任教宗访问美国后,总是被媒体形容为"带著分裂离开"。这是因为美国的天主教徒与罗马教廷之间常存在严重的立场冲突——尤其在文化议题上。他指出,美国天主教内部虽然仍有保守派存在,但整体趋于自由主义,与美国的保守派基督徒与犹太人无法完全融合。
他以半讽刺的口吻总结道:"我每天早上醒来,都感谢主我不是美国天主教徒。"
继续分析美国天主教徒的处境,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他们在信仰与现实之间的撕裂与精神紧张:
"我说美国的天主教徒有精神上的紧张,就像中国孩子不会用筷子一样。他们既是天主教徒,却又支持堕胎、同性婚姻和变性,这种信仰与行为的矛盾,怎能不导致精神分裂?所以我常常感谢主,我不是天主教徒。美国的天主教徒——他们真的有精神上的问题。"
他也指出,天主教的核心仍在欧洲,美国的自由派天主教徒,也难以找不到真正的信仰家园——他们所追求的"自由"其实背离了天主教信仰的核心。
不过他也观察到一种新趋势:现在美国天主教徒当中,保守派正在上升。这是绝对有的,而且他们已不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阵营。他们清楚自己无能为力,但仍有人在做梦希望能出现"女神父"。
在节目中,主持人提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方济各的神学理念,对欧洲、南美洲甚至全球的信仰与政治生态有何影响?
陈牧师作如下回应:
我认为这是相辅相成的。他既是这股"左转"潮流的产物,也反过来推动了这股潮流。其实,在约翰·保禄二世去世后,欧洲天主教内部召开过一次重要高峰会议,当时的关键人物大多已被委任为梵蒂冈的各类部长,如全球宣教部、教义部等(教义部过去由本笃十六世主理)。这些人好比美国白宫的内阁成员,握有实权。
这场会议做出一个"惊世骇俗"的决议:天主教要甘愿成为欧洲的"第二大宗教"。第一大宗教?不用说,就是伊斯兰教。
于是,欧洲的天主教全面撤退,把前线让给伊斯兰和世俗思潮。
他评价说:
"这就是欧洲后基督教时代的起点。若我们相信政治、文化背后有宗教的力量,那推动欧洲堤坝崩塌、洪水泛滥的,正是罗马天主教自己。这个信仰的撤退,是始作俑者。"
当然,他也承认:有时候,宗教也无法抵挡世俗洪水的冲击。当圣彼得广场都被世俗化的浪潮冲垮时,天主教也无能为力。最终的结果就是整个欧洲进入了"后基督教"时代,这是极其可怕的事。
他总结说:欧洲的今天,与方济各这13年的教宗任期有不可推卸的关系。方济各任内,神职人员集中在欧洲,而欧洲却正在把自己拱手让给穆斯林和共产主义。这些趋势与方济各的在位同步发生。
而更令人警惕的是,这股浪潮正向美国扩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