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全球逾12億天主教徒的精神領袖,已故教宗方濟各以其簡樸親民的形像贏得「人民的教宗」美譽。然而,在墮胎、變性、難民與倫理等社會議題上,他一再採取「包容」路線,引發部分保守派批評,甚至認為這種立場動搖了教會的神學根基與全球影響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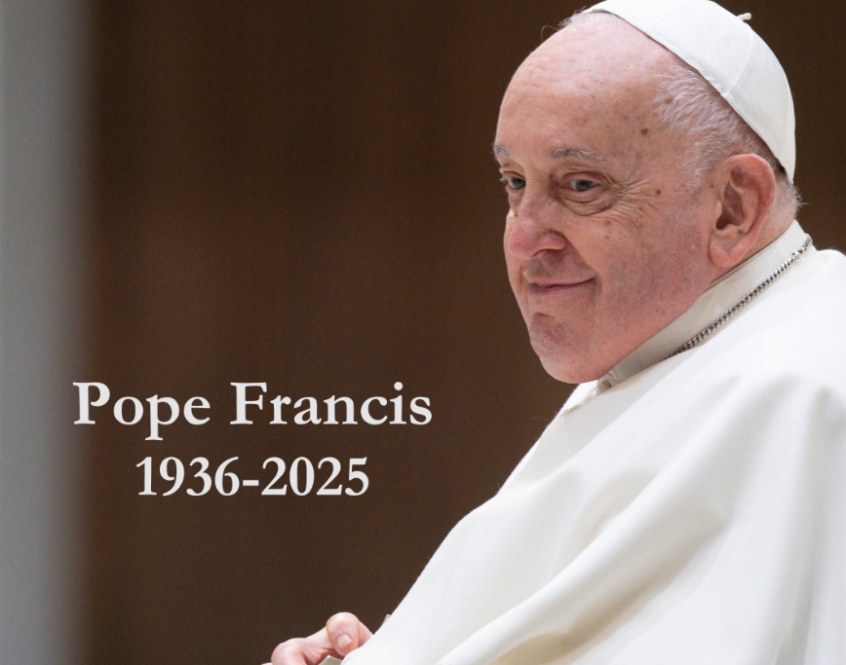
近日,旅美華人牧者陳佐人在《詢經問道》節目中發表評論,直指已故教宗方濟各在諸多爭議中「明哲保身」。作為美國西雅圖大學神學系教授,陳牧師擁有深厚的神學背景,曾師從天主教思想家特雷西(David Tracy),並長期在天主教大學執教。他以特有的幽默和洞察力,講述方濟各的生平,甚至調侃美國天主教的信仰困境,稱他們「難以找到信仰的家園。」
在陳佐人看來,教宗方濟各的人生軌跡與神學立場顯得頗具爭議。方濟各本人曾坦言自己並非神學家。陳佐人笑稱,方濟各「神學根基薄弱」,他16歲才成為修士,相較於許多自幼進入修道院的人,他的早年生活更為「世俗」——他熱愛足球、舞蹈,思想活躍。由於學科背景為數理化工,早年主要教授數學,自然難以建立起系統的神學架構。
在阿根廷服事期間,方濟各曾因持保守立場而受到同僚排擠,被迫調往偏遠鄉村任教。具體説來,就是方濟各曾對抗「解放神學」,反對其背後潛藏的馬克思主義傾向與「以救濟窮人為假口號」、實則面向將教會掏空的社會行動,因此受到同儕排擠,被迫離開主流。
方濟各後來因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提拔而重新回到主教序列,最終晉升為阿根廷大主教,並在2013年成為教宗。陳佐人稱方濟各是「保祿二世的勝利軍」,當時若望·保祿二世大力整頓自由派神職人員,尤其在美國任命了許多持守傳統立場的主教,形成一批至今仍影響深遠的保守力量。
然而,方濟各在教宗任內卻展現出完全不同的路線。陳佐人批評他在性別、社會、外交等議題上走「彩虹路線」,即傾向自由派、多元文化主義。他認為這背離了若望·保祿二世當年所堅持的教義立場。
此外,方濟各的過去也飽受爭議,尤其是他在阿根廷「骯髒戰爭」(Dirty War)期間的角色。所謂「骯髒戰爭」是指在20世紀70至80年代,阿根廷軍政府實行的極權統治與鎮壓行動。當時,在獨裁者統治下,許多異議分子、民主運動支持者、甚至普通公民被秘密逮捕、酷刑與處決。方濟各的神職生涯正與這一時期重疊,因此外界對他當時的角色有諸多爭議。
一些人批評方濟各在軍政府執政期間未能挺身而出,特別是在有兩位神父被捕並遭酷刑致死的事件中,質疑他未盡保護責任。然而,也有不少當時的證人及歷史資料指出,方濟各在極為危險的情勢下,曾通過各種方式掩護並救援多位神職人員,有些甚至因此倖免於難。雖然當時很多人期待他公開對抗政府,但他顯然採取了更隱蔽的策略。
陳佐人進一步指出,雖然有關方濟各是否涉入「骯髒戰爭」的爭議持續至今,但在他當選教宗之後,有數本重要傳記迅速出版,為其「洗白」形像。這些傳記引用大量人證,甚至包括昔日批評者,轉而稱贊他在獨裁政權下展現勇氣、營救受難神職人員。盡管如此,陳佐人用四個字來概括方濟各的人生風格:「明哲保身」。借用李嘉誠的説法,就是「在商言商」。
陳佐人指出,方濟各曾在接任本篤十六世之後對媒體表示,自己將效法本篤的榜樣,會在身體狀況不允許時主動請辭。但事後並未履行這一承諾,依然堅持在任,表現出對權力的眷戀。如今,方濟各在任期離世。陳佐人牧師認為方濟各「不守信用」,並半開玩笑表示,自己曾一度有衝動模仿電影《教父》場景,攜帶紅布前往梵蒂岡,站在教宗牀邊勸其「辭職」,強調「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在陳佐人看來,方濟各不僅戀棧權位,還在任內大幅加速任命紅衣主教,意圖在卸任後確保有繼承其路線的「克隆人」當選為下一任教宗。他將此比作拜登總統在任期末加緊提名法官以影響未來司法走向,認為方濟各的舉動同樣是「佈局身後事」,希望鞏固其神學與政治路線不被逆轉。
他進一步指出,教廷內部存在明顯的路線之爭:若望·保祿二世與本篤十六世代表保守主義陣營,而方濟各則代表激進派的徹底翻盤。這種「宮廷鬥爭」已成為梵蒂岡結構的常態,簡而言之,就是「保守派與激進派之爭」。
陳佐人藉此引出一個地緣政治的觀察。他指出,梵蒂岡雖然宣稱注重全球多元文化,尤其強調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代表性,但從紅衣主教的國家分佈來看,仍是歐洲中心主義。他建議查看維基百科的紅衣主教分佈列表即可得出結論:絕大多數紅衣主教仍集中於歐洲,甚至單個歐洲城市(如德國的科隆、法國的裡昂、意大利的都靈)擁有的紅衣主教數量,可能多於整個亞洲或非洲。
他進一步指出,即使選出非歐洲籍的教宗,其文化與種族背景也深具歐洲色彩。例如阿根廷雖位於南美洲,但長期被視為「非南美化」的國家,其人口主要為歐洲移民後裔,缺乏本地土著血統。這也解釋了為何二戰後許多納粹戰犯選擇逃往阿根廷,因為其種族與文化背景更接近歐洲。他以此類比為「上海人不能代表中國人」,指出「阿根廷教宗不能代表南美洲」這一看法在拉美本地普遍存在。

陳佐人繼續分析指出,理解天主教的結構與教宗的選舉,必須從「宮廷政治」的角度來看,不能只用神學或屬靈的眼光去理解。他強調,梵蒂岡的「社會道德價值觀」是不可動搖的,如同鐵軌一般,即使是教宗本人也無權越雷池一步。例如,天主教堅定反對墮胎、同性婚姻、變性行為等,這些被視為「天條」,哪怕是方濟各也無法公開違反。
雖然方濟各在某些議題上顯得立場模糊,例如曾對同性戀伴侶表達「祝福」,但他從未明確反對同性婚姻,也未推動女神父制度的合法化。陳佐人指出,即使方濟各一度有意在其任內突破這些教義底線,他周圍的紅衣主教「也會鎮住他」,可見教廷內部的力量制衡非常強大。他形容教宗「有如毛澤東」,而其身邊的人則如同「周恩來」,掌握著實際的戰略與操盤權,暗示周邊顧問可能比教宗本人更有實質影響力。
進一步談到教宗的「實權」時,陳佐人認為,雖然方濟各在教義上不能隨意更動,但在外交領域卻大有可為。他類比美國總統指出,教宗在「外交與關税」般的領域具有主導性,其中最關鍵的議題之一就是「中梵建交」。他説,這關繫到是否選出一位「中粉」的教宗。如果教宗親中,「中梵建交就像搭上日本的子彈列車,會被加速推進」;反之,如果繼任者如若望·保祿二世那樣堅定反共,那這個議題就會被「冷藏在地窖裡,永不見天日」。
盡管如此,梵蒂岡的道德立場仍然牢不可破。他強調,這些核心倫理立場是由教宗若望·保祿二世(John Paul II)以教宗文告的形式定下來的,其中最具標志性的就是《神聖的生命》(Evangelium Vitae)。這篇文告堪比《美國獨立宣言》,確立了天主教社會道德的主線。因此,即使是改革傾嚮明顯的方濟各,在美國也無法贏得廣大天主教徒的認同。
陳佐人指出,美國擁有約6500萬天主教徒,但歷任教宗訪問美國後,總是被媒體形容為「帶著分裂離開」。這是因為美國的天主教徒與羅馬教廷之間常存在嚴重的立場衝突——尤其在文化議題上。他指出,美國天主教內部雖然仍有保守派存在,但整體趨於自由主義,與美國的保守派基督徒與猶太人無法完全融合。
他以半諷刺的口吻總結道:「我每天早上醒來,都感謝主我不是美國天主教徒。」
繼續分析美國天主教徒的處境,他直言不諱地指出他們在信仰與現實之間的撕裂與精神緊張:
「我説美國的天主教徒有精神上的緊張,就像中國孩子不會用筷子一樣。他們既是天主教徒,卻又支持墮胎、同性婚姻和變性,這種信仰與行為的矛盾,怎能不導致精神分裂?所以我常常感謝主,我不是天主教徒。美國的天主教徒——他們真的有精神上的問題。」
他也指出,天主教的核心仍在歐洲,美國的自由派天主教徒,也難以找不到真正的信仰家園——他們所追求的「自由」其實背離了天主教信仰的核心。
不過他也觀察到一種新趨勢:現在美國天主教徒當中,保守派正在上升。這是絕對有的,而且他們已不再是一個整齊劃一的陣營。他們清楚自己無能為力,但仍有人在做夢希望能出現「女神父」。
在節目中,主持人提出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方濟各的神學理念,對歐洲、南美洲甚至全球的信仰與政治生態有何影響?
陳牧師作如下回應:
我認為這是相輔相成的。他既是這股「左轉」潮流的產物,也反過來推動了這股潮流。其實,在約翰·保祿二世去世後,歐洲天主教內部召開過一次重要高峯會議,當時的關鍵人物大多已被委任為梵蒂岡的各類部長,如全球宣教部、教義部等(教義部過去由本篤十六世主理)。這些人好比美國白宮的內閣成員,握有實權。
這場會議做出一個「驚世駭俗」的決議:天主教要甘願成為歐洲的「第二大宗教」。第一大宗教?不用説,就是伊斯蘭教。
於是,歐洲的天主教全面撤退,把前線讓給伊斯蘭和世俗思潮。
他評價説:
「這就是歐洲後基督教時代的起點。若我們相信政治、文化背後有宗教的力量,那推動歐洲堤壩崩塌、洪水泛濫的,正是羅馬天主教自己。這個信仰的撤退,是始作俑者。」
當然,他也承認:有時候,宗教也無法抵擋世俗洪水的衝擊。當聖彼得廣場都被世俗化的浪潮衝垮時,天主教也無能為力。最終的結果就是整個歐洲進入了「後基督教」時代,這是極其可怕的事。
他總結説:歐洲的今天,與方濟各這13年的教宗任期有不可推卸的關系。方濟各任內,神職人員集中在歐洲,而歐洲卻正在把自己拱手讓給穆斯林和共產主義。這些趨勢與方濟各的在位同步發生。
而更令人警惕的是,這股浪潮正向美國擴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