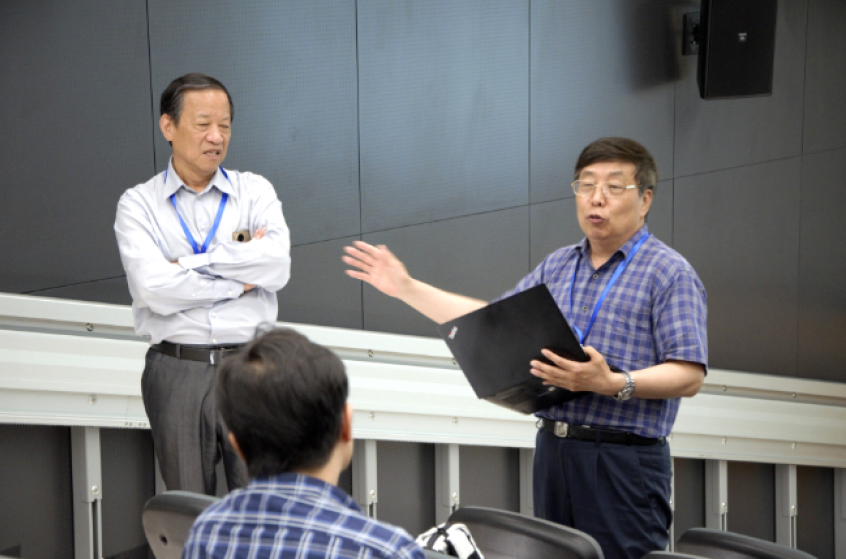
2025 Logos International Forum (LIF)5月3日在浸會大學舉行。其中信仰與中國文化論壇已連續舉辦三屆,致力推動在華基督教的處境化運動,促進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通過對談進行交流。今年論壇分為上下半場:上半場聚焦於儒家文化中的「君子理想」與基督信仰中的「信徒典範」,促進雙方思想的互動與碰撞。下半場則聚焦「死亡與永生」的主題。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王中江與台灣輔仁大學曾慶豹教授展開精彩對談,分別基於中西哲學與宗教的深厚傳統,圍繞人類對長生、不朽與永生的不懈追求與深刻思考,展開了一場富啟發性的對話。
王中江教授: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多元不朽觀
在論壇中,王中江教授首先從中國歷史文化的背景出發,系統梳理了「不死」觀唸的演變。他指出,從秦始皇和漢武帝對「不死之藥」的追求,到道教煉丹術的盛行,以及對神仙境界的嚮往,這些現象都反映了人類對超越生命有限性的渴望。這種渴望不僅存在於帝王將相之中,也遍及社會的各個階層。
所有事物都在不斷變化中;變化過程中的各種可能性可以相互補充,形成「互補性原理」。最後他強調,人類擁有獨特的主觀能動性和強大的意志力,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影響甚至改變命運。他引用道教經典《抱朴子》中葛洪的名言「我命在我不在天」,強調了這種積極追求的理念。葛洪認為,通過煉製仙丹等方式,可以獲得補益身體的能量,實現長生和成仙。其核心思想是,人類的主觀努力能夠改變自然的固有進程,突破生命的侷限,實現延壽甚至不死的目標。
後來,道教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提出「與道同久」和「道人合一」的理念,認為通過堅持本源之「氣」,可以達到與宇宙共存的至高境界。
隨後,王中江教授轉向老莊哲學的時間觀念。他指出,老子哲學包含兩種時間觀:一種是與「道」相關的超越性永恆時間,體現在「恆」、「久」與「不死」(如「穀神不死」)等概念中;另一種則是具體事物的有限時間,表現為生老病死、新陳代謝等自然規律。
王教授解釋,萬物由「道」創造,因此在誕生時便攜帶了一部分「道」的時間屬性,但自身的時間是有限的。然而,老子哲學中的「道人合一」和「道物合一」理念,為個體超越生命的有限性、追求無限提供了可能性。
他特別強調,老子所説的「不死」或「永生」,主要是指精神層面的不朽。正如「死而不亡者壽」所揭示的,這種「永生」並非肉體生命的無限延續,而是指個體的價值、思想或品德能夠長存於人心,並被歷史記住。
王教授還提到,莊子在其著作中描繪的「真人」和「神人」等理想人格,以及「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境界,也反映了對精神性永恆的深刻嚮往。
接著,王教授探討了儒家對生死的獨特態度。儒家主張「未知生,焉知死」,以務實的精神把重點放在人生的當下,認為只有先深刻理解「生」的意義,才能更好地理解「死」。在儒家看來,死亡不一定是負面的,例如孔子就把死亡比作一種「大休息」。
此外,王教授提到儒家追求不朽的方式,主要體現在「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他也提到胡適對「不朽」的現代理解,認為個人通過融入社會,承擔歷史責任,就能實現「人人皆可不朽」。儒家還通過生命的代代延續、祭祀祖先(「慎終追遠」)、文化傳承,以及「天人合一」的思想,展現其多元化的不朽觀。儒家對道教以自然生命為核心的生死觀,也抱持一定的理解和認同。
最後,王教授簡要提到佛教的生死觀。他指出,佛教的死亡觀基於其「緣起」理論,認為生命的本質是「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輪回是佛教理解生命流轉的重要概念,而最高的覺悟「涅槃」,則是徹底超越時間束縛,達到「無時間性」的終極解脱。王教授認為,通過比較不同文化和思想體系中的生死觀,可以促進相互理解與學習。
曾慶豹教授:基督教神學視野下的「死亡」與「復活盼望」
曾慶豹教授從基督教神學的角度,對死亡與永生的議題進行了深入探討。他指出,在現代社會,「死亡」仍然是人類感到無力且無法解決的終極難題。回顧人類文明發展的歷程,無論是建造宏偉的建築、繁衍後代、科技進步,還是思想文化的創造,其背後的動機多多少少都與對死亡的回應和抗爭有關。這些努力的核心目標,是追求某種形式的「不朽」,即使只是暫時地克服疾病,也反映了對抗死亡的渴望。
曾慶豹教授強調,基督教對「生」與「死」的議題有深刻探討,並將「死亡」放在其教義核心。基督教的上帝是一位「會死的上帝」,這一看似違反常識的觀點,打破了許多傳統宗教中認為神明「不死」的固有觀念。在基督教神學中,上帝的「死」(特指耶穌基督的死亡)並不是絕對的終結,而是一個具有轉折意義的關鍵點——既是舊的結束,也是新的開始。
基督教在此基礎上探討「永生」的概念。曾教授指出,基督教所説的「永生」對死後世界的具體描述其實是模糊的,更像是一種充滿期盼的展望。但更重要的是,關於「永生」的討論,焦點不在死後的狀態,而是回到當下的「生」。換句話説,基督教更關注的是死之前的問題——我們該如何活,如何面對必然到來的死亡,而不是死後的情況。因是「活人」才談論死亡,而非「死人」在談論死亡。
援引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爾的觀點「人是走向死亡的存在」(Being-towards-death),曾教授説明「活著」這件事情本身就內在地包含了對死亡的朝向。他認為,基督教是一個「向生」的宗教,其所有關於死亡的談論,最終都指向「生」的意義與價值。因此,基督的死並非一個句號,而是緊接著「復活」。基督教最核心的節日——「復活節」的意義正在於此:所有的受難,都預示著一個新的開始和可能性。
那麼,如何理解「復活」?曾教授指出,基督的復活並非指向身體在原有實體層面的簡單復原,而是開啟了另一種超越我們對身體凡俗想像的存在方式。因此像「空墳墓」的物理證據,並非信仰的根本障礙或唯一依據。復活的真正意義在於:死亡從此不再僅僅是一個終點,它開啟了一種改變,開啟了一種對未來新的、可能的期待。時間因此擁有了一個「未來」的向度,而這個未來並非與現在毫無關聯。對「復活」的理解,往往需要從復活的視角來回溯和審視死亡,是復活的信念深刻地影響了人們對死亡的態度。
曾教授進一步解釋了莫爾特曼(Jürgen Moltmann)的「盼望神學」(Theology of Hope)。這一思想強調,我們時間向度中的一切都指向一個「將來」。一旦我們對未來抱有希望和期待,這種希望就會反過來幫助我們重新審視現在,給我們勇氣面對恐懼與害怕。只有對於將來前景存盼望,我們才能克服當下的困境。因此,單純追求肉體上的「不死」,有時反而顯得荒謬,因為「死亡」本身可能才是更新的契機——一種事物的結束往往意味著另一種新事物的開始。上帝的「死」是是如同常人一樣的死亡,正是這死亡才讓所有人能感受到上帝與他們同在,而非高高在上的神。因此死亡是有意義的,它賦予了人生一種獨特的意義框架,同時也開啟了一個復活的新盼望。死亡不是終結,而是一個轉折,關鍵在於它通向的是永生還是永死。
最後,曾教授提到馬克思對「德國的復活日」的比喻。的比喻。他認為,馬克思用這個比喻來形容理想社會的到來,表達了對人類苦難的關懷和對自由的追求。在這裡,「復活」象徵著戰勝恐懼,尤其是戰勝死亡這一最大的枷鎖,讓人成為真正成熟和自由的個體。這與基督教信仰中「復活」戰勝死亡的精神,在某種層面上產生了共鳴。
在兩位講員結束各自的闡述後,研討會進入了熱烈的問答與評論環節。針對與會者提出的關於生命定義、儒家生死觀、馬克思與宗教、科學與永恆以及耶穌復活等多個議題,兩位講員分別給予了回應。
信仰與中國文化論壇論壇採用的形式是圍繞主題框架,邀請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領域的知名學者分別發表觀點,並進行對談。會後,會議將組織學者對整個對談撰文評議,並在公開學術雜誌發表。
相關報導
信仰與中國文化論壇:「儒家君子」與「基督信徒」的跨界對談
浸大第十屆LOGOS論壇 中港台美學者對談信仰、文化、科學及社會議題
前跨國企業高管談領導力 葉志易:把變局化為「六重契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