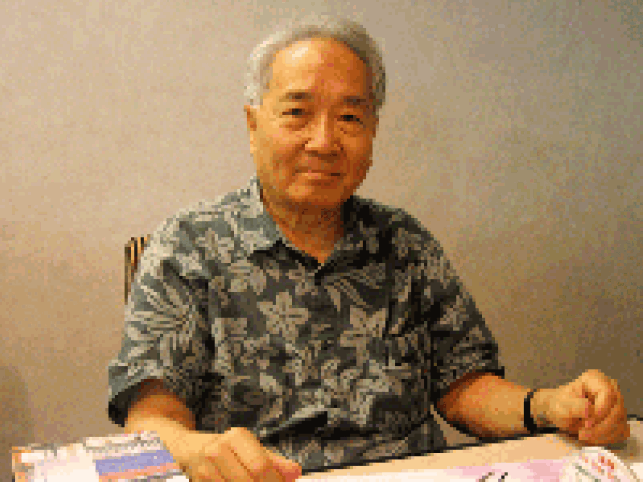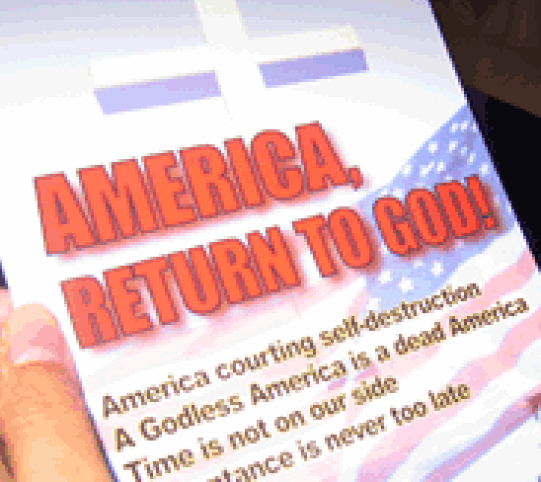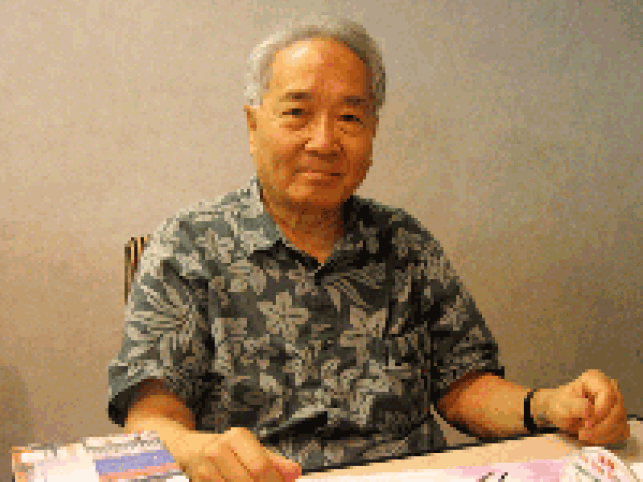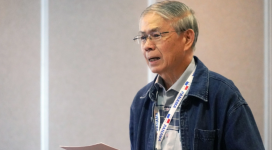為了參加「普世教會事工推進會」創辦人張子華牧師的紀念活動,「大使命中心」會長王永信牧師近日專程到訪香港。在上週日他的80大壽的慶祝聚會裡,王牧師分享了他的未來事奉的方向。雖已屆晚年,他仍盡用心力於福音和宣教事工上,事奉神的熱情絲毫未有減退。
今天本報有幸邀得王牧師在緊迫的日程擠出一點時間,與本報做了一次專訪。他一生的事工、現今教會的問題、美國的問題、以及香港的信仰情況,都一一與本報分享。
王牧師,您先後創辦了不同的事工-—中信、洛桑、華福、大使命中心,和近年的「基督徒關懷社會基金會」、「支持一男一女婚姻協會」等。在上次你80大壽聚會上,您見證説自己的事工的方向上並沒有事先計劃。那麼,現在你回頭看,你覺得這些不同時期開展的事工之間有著什麼關係?
是的,我自己沒有預先的計劃。我每走一步,神就給我開一扇門:神知道我的需要是什麼。他先訓練我,然後給我下一步;祂再訓練我,又再給我下一步。.如果沒有中信,不可能有洛桑;如果沒有中信的經驗,我不能作洛桑。中信是在美國教會開始,華福是向著世界的華人教會。所以,沒有中信的經驗,就沒有華福。同樣地,沒有洛桑,也不會有華福。沒有華福,就不會有「主後二千福音運動」(AD2000 & Beyond Movement)。
雖然是神開路,但是祂有祂的計劃,一步一步的訓練我。God knows what He is doing。
回想這幾十年,您覺得最難推動的是哪一個事工呢? 困難在哪?
其實,都困難,但有最困難的,就是打破傳統——華人很多的傳統、觀念和習慣。在華人中,推動大家合作很不容易。
這有兩個原因:第一,華人愛家庭的傳統是全世界有名的。師母(王永牧師的太太)以前在香港生活的時候,她去九龍城的市場買菜,她跟賣菜的老人家談話,得知他有兩個女兒,一個在美國,一個在英國。他們為了供養他們的女兒辛苦地工作。這是中國人的美德和傳統:家裏的父母吃苦,支撐和凝聚著一個家。
但這同時有副作用,就是形成我們內向的文化。我們從小都是「家」的文化:各家自掃門前雪,但家以外的就不多管。
但我們成了基督徒,也把這種傳統不知不覺也帶到教會來。信徒只每個星期去教會,教會以外和宗派以外的教會則沒有來往。因此華人教會一體和合一的情況很差。
第二就是教導。教會的教導中,對「教會」這兩個字的意思是理解不全面。
「教會」指的是面前看得見,摸得到的本地教會,但教會還有第二個意思的。但我發現教會沒有講這個,牧師講道時也沒有教。教會的意思還指「普世的教會」,但這教會指的是「相信聖經的教會」,現在有不相信聖經的教會,那些就不用談了。
很多教會只教導了第一個意思。牧師都説要愛教會、服侍教會,如此大家想到的只有自己的堂會,卻少談我們的整個身體-—the universal body of Christ——這是主整個的身體。這一層意思教會很少講,所以弟兄姊妹整天都在自己的教會裏,對於整個身體的關心很少,這是第二個原因,造成了今天教會欠缺神的國度的觀念和心胸不夠廣闊。
那麼,教會可以怎樣突破這種狀況呢?
要突破的話,牧者先要有突破;牧者要有突破,神學院先要有突破。神學院的領袖老師開始要先有廣大的心和國度觀念-—the Kingdom Concept——這是華人教會很缺乏的。
提到神學院,台灣有基督教媒體批評現時的神學院未能提供他們所需要的人,學生欠缺媒體和資訊方面的專業知識。你對這個問題有什麼看法?您認為今天的神學院具體應該進行哪方面的改革呢?
神學院和教會都説要有partnership,強調知識和靈性並重。但事實上,神學院都走知識、學問和學位的道路。基督教不是反知識的。一個事奉主的人必需在知識和屬靈生命上有一個平衡。
至於改革,其實就是整個神學院和教會世界觀的改革,有了這個作為一個基礎,再談該怎麼作;就是説,先要看見我們今天所要作的到底是什麼。我們知道我們要作的是什麼時,才有真正的方向和目標。這樣才能知道我們教會要找什麼樣的傳道人。他們知道了以後,神學院才知道要供應怎樣的傳道人。
你明年二月將會出版一本書,書名叫「America Return to God」,這本書是針對美國哪方面的問題呢?
從16世紀開始,人文主義興起。簡單來説人文主義就是抬高人、講自我,把神的地位降低,所以這主義叫humanisum——the emphasis is on man。所以從16世紀起,人是萬物的尺度,人的自我提高。在19世紀未,自由主義新派的學者起來,他們不相信聖經是神的話,不相信耶穌是聖靈生的兒子,不相信基督的神性,慢慢就演變成一個情況:人不需要神。
美國是神建立的,美國開國的元老都是基督徒。美國鈔票上都印有「In God, We Trust」—-我們相信上帝。但最近50年,他們離神越來越遠了。美國的公立學校現在不容许禱告、讀經和講福音,法院內不準掛十字架和誡命,他們説不要宗教了,更不要基督教了,所以美國離神越來越遠。
西歐離開神,美國則跟著西方走。加拿大亦然。我們看著這樣的危機,我們要出一本書。我們盼望這書明年二月能出來,把它寄給美國各階層的領袖。我們希望,我們作為今天約拿的角色,引領人們悔改。
這次您來香港,您覺得香港的教會氣氛怎麼樣?
第一,香港的思想和錯覺走在前面,對於美國和加拿大的華人,這些則在後面。就是説,香港人對於自身的觀察很敏鋭;第二,這裏滙聚華人教會的精英,所謂精英就是人才。
前面講的都是好處。後面講的就是不好的地方。
第三,這裏有自守的情況,外展很缺乏。可能受了環境的影響吧。有中國—-「老大哥」在旁邊,在他們心裏某程度上受到了影響;不要因為大小環境的情況變成內向,要往神的國度展開。
第四,我覺得香港的教會在聖經的根基上要站得住。拿同性戀問題為例,教會的觀點就跟聖經不一樣了。聖經已經講得很清楚:同性戀是罪,但他們不斷的繞圈子,説:「聖經雖然這樣説,但是什麼什麼……」,他們有「但是」。
教會跟著世界走。有一句話説得很對-—教會怕得罪人,但是不怕得罪神;教會寧可得罪神,不怕得罪人。他們跟著大眾走,大眾的意思怎樣,領袖就跟著走,沒有道德原則和信仰原則,隨著羣眾走。為要得著支持和選票。這是教會可悲的現象,這是民主國家的可悲現象。
所以我常説:「民主和獨裁都是人本主義」。人家常問我為什麼這樣説。民主和獨裁,兩邊都是人本主義,分別只在於獨裁是一個人,民主是一羣人,但説來説去都是人本主義。
民主制度是人所能發明的政治體系中最好的。Best political system conceived by man. 但是,民主有它的極限,the limitation of democracy。為什麼?「多數統治」,這個思意的根基是:一個、兩個可能會錯,但多數不會有錯。這個體制在一個好的基督教背景下可以維持一段時間,但當大多數的人都敗壞了,那怎麼辦?這個民主還有什麼盼望?就像現在比利時、荷蘭、丹麥、西班牙和北歐等國都是同性結婚合法的國家。看看加拿大,美國也跟著他們走。我們要注意到這些全都是經過多數人通投票過的法例,都是通過了民主的手續而生的。
所以,不能用民主的方法解決問題,因為民主還是人本主義,所以説到底,還是要回歸神。人是可敗壞、可沉淪的——不管是一個、還是一羣。所以我們要回到上帝面前。
後記
眼前的王永信牧師説話十分有「中氣」,一點也不像年屆80的人。王牧師多年來靠著絕對的信心開始了不少具歷史性的華人事工,他的信心影響了整個華人基督教界。看到他的白髮,只能想到箴言裡的一句話:「白髮為老年人的尊榮」。